今天,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来自美国的小威廉·凯林教授(William G. Kaelin, Jr.)、格雷格·西门扎教授(Gregg L. Semenza),以及来自英国的彼得·拉特克利夫爵士(Sir Peter J. Ratcliffe),以表彰这三位科学家在细胞低氧感知与适应研究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 2019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官宣”图(图片来源:https://www.nobelprize.org)
我们平常会缺氧吗?细胞为什么要有低氧感知的能力?细胞感知到低氧之后又会做出哪些响应动作?这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咱们不妨从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说起。
比食物和水更重要的 是氧气
今年国庆假期,几部国产大片成为人们去电影院的首选。其中之一便是《攀登者》,讲述了我们中国登山队员克服重重困难,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感人故事。大自然带给他们的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狂风、寒冷、低氧。

△ 怀抱氧气罐的“攀登者”(图片来源:微博@费启鸣)
我也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对其中低氧的问题感触很深。每当登山队员们到达珠峰上的某个地标,大银幕上就会给出此处的风速、温度,以及氧含量。在珠峰上,氧气含量只有9%左右,不及平原水平(20.8%)的一半。处在这种低氧环境中的感觉,大概就像是平常不跑步的人刚刚跑了几公里之后的感觉差不多——无论你怎么使劲喘气,都觉得自己喘不上气来。此时,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我缺氧!!!”
我们的身体可以十几天不吃饭,也可以几天不喝水,却一分钟也离不开氧气。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司空见惯的常识,无须解释。

△ 对身处太空的宇航员来说,“爱的供氧”一刻都不能停止(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可究竟为什么氧气如此不可或缺呢?答案在于:我们需要氧气来完成食物的“燃烧”。

△ 有氧呼吸的过程可以简单归纳如上,但实际上的过程更为复杂(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然,你的任何一个细胞里也没有正在燃烧的小火苗。但其实,食物中的能量物质正是通过与氧气完成的氧化反应才得以释放能量的。从化学上来讲,这跟一块木头的燃烧可以说是一码事情,主要的区别在于:可见的燃烧是个剧烈的氧化过程,而细胞里的“燃烧”是个受控的缓慢氧化过程。
无论是能量物质还是水,我们的身体里都有不少储备。唯独氧气,我们是几乎没有“余粮”的——事实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没有额外单独存储氧气的能力。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很难回答,更难以求证的问题。但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氧气比水和食物都更容易获得。既然你一张嘴就能得到它,何必要进化出一个氧气罐来呢?
但是,也恰恰是氧气这种张嘴可得的特性,把细胞给惯坏了。它们都习惯了正常生活环境中的供氧水平,一旦遭遇“低氧”的特情,细胞们就要开始抗议了。不过,我们的身体也有各种手段来解决低氧的麻烦。
由氧气催生的兴奋剂
我们最常遭遇的缺氧,显然不是登上高原时才会遇到的那种情况,而是在你剧烈运动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对于这种临时性的缺氧,我们的身体也有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以求迅速解决问题。
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心跳加速,通过更快的呼吸和更快的心跳,提高供氧速率。另外,我们血液中的红细胞也会合成一些特殊的小分子物质,它们能够结合到血红蛋白上,提升血红蛋白输送氧气的效率。

△ 最左侧的血细胞是红细胞,它的出现是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不过,临时手段也有临时手段的问题,肯定不能长期采用。所以当你身处高原环境,每一个细胞都长时间缺氧时,你的身体就要另谋他策了。
最先被科学家们观察到的现象是,我们体内的红细胞数量会大大增加,以此提高运送氧气的能力。简单来说,一个车队的卡车多了,运力自然就提高了。其实,增加卡车数量是个很好的策略,像鲸豚类水生哺乳动物,因为不能利用水中的氧气,也只能通过提高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的数量来加大携氧量。
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当我们长期处在低氧环境中时,肾脏就会合成EPO这种糖蛋白激素,而EPO会刺激骨髓制造更多的红细胞,以此来应对低氧问题。

△ EPO的三维“彩照”(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EPO被发现之后,它很快就被应用于临床,医治与贫血相关的多种疾病。在上个世纪末,人们又为EPO找到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应用方向——兴奋剂。通过注射EPO,运动员的身体就会合成更多红细胞,提高供氧能力,从而提高肌肉的输出功率。这效果就像是汽车打开涡轮增压一样,单纯通过提供更多的氧气,就能从同样的燃料中榨出更多的能量来。
不幸的是,EPO因为是一种蛋白质,几乎不会直接从尿液中排出,所以很难从尿液中检测到。即便是从血液中检测,起初也很难分辨运动员自己身体合成的EPO与外来的人工生产的EPO。目前的主要检测手段是通过专一性的抗体来分辨两者。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又有了实验室级别的前沿生物学手段,在基因级别上直接调控细胞的EPO生产水平,让运动员的细胞能够自行生产出更多的EPO来。显然,面对这种“自产自销”的EPO,兴奋剂检测必须要应对更为艰巨的挑战。
谁操纵了细胞里的低氧应答?最早进行EPO基因操纵实验的人,恰恰就是今天的诺奖得主之一,西门扎教授。

△2019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科得主之一Gregg L. Semenza(图片来源:https://www.pnas.org )
他的实验室将人的EPO基因转移到了小鼠体内,结果这种转基因小鼠就能生成更多的红细胞了。
这一结果说明了两件事儿:一、EPO能够促成红细胞的增多;二、人跟小鼠的EPO差别不太大,换着也能用(这可不是放在所有蛋白质上都能成立的事情,事实上,两者只有80%左右的一致性,不过这在生物学角度上来看已经算是相当高的近似性了)。
但是,西门扎教授并不满足于此。一个很简单又很直接的问题就是:低氧这种环境变化是怎么转化成EPO合成这个应答动作的呢?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细胞怎么感知“低氧”这件事?第二、细胞怎么提高EPO的合成水平?
很多科学大家都会告诫年轻人:选择课题的时候要认清你这个领域当前的发展水平,选择一个当前的发展水平能够解决的问题来研究。西门扎教授无疑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选择的就是去研究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细胞调控EPO合成水平的方式。在当时,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对于基因的调控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具备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
前文曾经提到,EPO是一种糖蛋白激素,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都是细胞依据基因的编码来生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告诉我们,人类大概有2万个左右的基因。但是,细胞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按照这2万个基因生产2万种蛋白质。事实上,这些基因中的大部分平常都是不工作的。说得更通俗一点,它们就像是压根不存在一样。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基因就像是被关上了一样。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细胞中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关闭一个基因。其中较早被人们所知的是转录调控因子。简单来说,在承载基因的DNA链上,位于基因上游的某个区域决定着这个基因的“开”与“关”,称为调控元件。而有些蛋白质能够结合到调控元件上,控制了基因的开关状态,称为转录调控因子。
西门扎和他的研究组首先找到了EPO基因上游的调控元件,并命名为低氧应答元件(hypoxia response element),因为它在低氧下就会开启EPO基因的表达。有趣的是,如果把这个元件序列移到其他与低氧无关的基因上游,这些基因也会在低氧状态下被开启。
随后,西门扎又找到了与低氧应答元件相配合的那个调控因子蛋白,并命名为低氧诱导因子1(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 HIF-1)。如果说低氧应答元件是与低氧应答有关的那个“开关”,那么HIF-1这个蛋白质就是操纵低氧应答开关的那只手。
左手和右手
准确来说,是那“双”手。
西门扎发现,HIF-1其实是由两个蛋白质组成的,于是分别命名为HIF-1α和HIF-1β。不过,两者之中的HIF-1β其实是一次“再发现”。
科学史上再发现的案例数不胜数,最经典的就是孟德尔在豌豆实验中发现遗传规律的故事。如果不是三十多年后其他科学家也独立做出了同样的结果,并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那么孟德尔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广为世人所知了。
当生物学远离了人工授粉和数豌豆的工作,步入基因与蛋白质的分子时代之后,再发现的事情有增无减。生物学家们往往在研究某一个问题时鉴定出了某个基因或蛋白质,却发现它其实已经在别人研究另一个问题时被发现过了。这也导致了一个令很多学习生物学的学生感到困扰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基因或蛋白质都有好几个名字。
HIF-1β就是一个让生物学学生头痛的蛋白质,他的“别名”至少还有:ARNT,TANGO,bHLHe2等等。为什么它的名字会这么多呢?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HIF-1β通过与不同蛋白质搭配,就可以去拨动不同的基因开关,于是它在不同方向的研究工作中被一次次重新“发现”。也就是说,HIF-1β有着多种重要的基因调控功能。
就在两年前,201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生物学家杰弗里·霍尔(Jeffrey C. Hall)、迈克尔·罗斯巴殊(Michael Rosbash),以及迈克尔·杨(Michael W. Young),以表彰他们在生物节律研究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在人体的生物钟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蛋白质称为Clock,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在生物钟系统中的重要性。而这个Clock蛋白需要与一种名为bHLHe5的蛋白质联手,才能发挥调控基因的作用。看看名字就知道,bHLHe5与别名bHLHe2的HIF-1β是非常类似的蛋白质。

△ 两只“手”(图片来源:https://www.haaselab.org)
事实上,西门扎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发现,无论是HIF-1β还是HIF-1α,两者都具有多重功能,共同管控着多种基因的开启。这些基因当中除了促进红细胞合成的EPO之外,还包括促进血管生长的VEGF、促进细胞摄入葡萄糖的GLUT1等等。总而言之,低氧状态会通过HIF-1α和HIF-1β这双“手”,开启一系列的基因,让身体从多种角度去应对低氧带来的能量供给困难。
“左手”太多有麻烦
所谓“非常措施”,自然不是常态。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来说,低氧这种非常状态所引发的身体反应,也可能有着潜在的伤害性。
二十世纪中叶,研究人员发现一类遗传性肿瘤病人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VEGF和EPO等激素水平极高,如同始终受到了低氧刺激一样。在这些蛋白质的作用下,他们大都患有不同部位的血管瘤,或是肾癌。这种病以最初描述此类病症的两位医生名字命名为冯·希佩尔-林道病(Von Hippel-Lindau disease,VHL)。
由于VHL病具有家族遗传性,极有可能是由一个特定的致病基因所引起的。科学家们通过基因的定位和测序,最终确定了与这一疾病相关的基因,并命名为VHL基因。

△ VHL基因发生突变,导致pVHL蛋白改变,无法与HIF1-α结合(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VHL病人的体内,VHL基因出现了突变,生产出来的VHL蛋白无法正常工作,于是就导致了VEGF和EPO蛋白含量的提高。VHL会与HIF-1有关系吗?又会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 2019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科得主之一 William G. Kaelin Jr.(图片来源:https://www.lilly.com)
今天的诺奖获得者之一,凯林教授在研究中发现,VHL出了问题,HIF-1α就会长期存在下去。而原本在正常细胞当中,只要氧供给正常,HIF-1α就会不断被细胞自己降解掉。
也就是说,细胞其实一直都在生产HIF-1α这只“左手”,但又不断砍去这只“左手”。而这把砍手的斧子就是VHL。在VHL病人的细胞里,VHL基因出了问题,生产出来的VHL蛋白是残次品,砍不断HIF-1α这只“左手”,于是细胞便始终处于受到低氧刺激的状态。

△ 2019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科得主之一 Sir Peter J Ratcliffe(图片来源:http://www.ox.ac.uk)
今天诺奖的另一位得主拉特克利夫教授进一步研究发现,VHL是一个E3泛素连接酶,专门负责给HIF-1α蛋白打上泛素这种标签。细胞里有一套独特的蛋白处理机制,能够将打上一串泛素标签的蛋白质分解掉。这是细胞处理无用蛋白,将原料回收利用的重要方式。当VHL出问题时,HIF-1α无法再获得泛素标签,也就无法再被细胞分解处理掉了。
细胞里的化妆师
故事讲到这儿,三位诺奖得主都出场了,但其实还是没有回答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细胞到底是如何感知“低氧”这件事儿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仍旧是拉特克利夫教授。
给蛋白质打上泛素标签这件事,生物学上称之为“翻译后修饰”。说白了就是给已经生产出来的蛋白质额外化点妆。不过细胞中并不仅仅只有泛素化这一种修饰,还存在磷酸化、甲基化、羟基化、乙酰化等等很多修饰方式,就像是化妆也分不同部位,同一部位也分不同的化妆方法。
拉特克利夫教授最初是想看看HIF-1α的泛素化与其他修饰种类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最初盯上了细胞中很常见的磷酸化,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有其他实验室的研究发现,HIF-1α首先要在特定位置被羟基化,然后才能被VHL识别,加以泛素化。打个不合适的比方,某人出门要先花个淡妆(羟基化),才能被化妆师(VHL)认出来,然后才能由化妆师化个浓妆(泛素化)。纯粹只是个比方,切勿对号入座……
拉特克利夫教授深入研究之后发现,负责给HIF-1α进行羟基化的化妆师是一种双加氧酶。顾名思义,这件事儿里涉及到添加氧的反应。于是,当细胞内氧含量不足时,这个反应很难进行——再好的化妆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至此,细胞对低氧的感知与响应链条就完整了。

当环境长期低氧时,细胞内氧含量也会下降,于是HIF-1α无法发生羟基化,也就不会被VHL加上泛素标签,也就不会被细胞降解掉。此时,完整的HIF-1α与HIF-1β结合,双“手”合璧,开启EPO、VEGF、GLUT1等基因的表达,让身体产生这些蛋白质,进入应对低氧的工作状态。
细胞的低氧与肿瘤的生存
补全低氧感知链条的拉特克利夫教授有着爵士的头衔,也是牛津大学若干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同时,他还是一位癌症领域的临床医生。其实他对低氧问题的兴趣,最初就是来自于他对肾癌等癌症的研究。他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肿瘤区域会出现大量的VEGF和GLUT1等蛋白质,而如果将HIF-1这双开启基因的“手”破坏掉的话,不但这些蛋白的含量明显下降,就连肿瘤的生长也会大大放缓。
今天的诺奖公布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不知道细胞的低氧感知有什么重要性。其实,它不仅仅与你的高原之旅有关系,还与肿瘤的生长和恶性化有着重要的联系。因为肿瘤之中正是一个低氧区。
我们都知道,肿瘤是细胞不断增殖的结果,老百姓俗称“大肉瘤子”。实际上这话很形象,因为这一堆细胞在一起就是一块肉。可是真正的肌肉组织里有血管和毛细血管,为每一处的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带走二氧化碳和其他代谢废物。而一个“肉瘤子”里面是没有血管的。因此,可以说肿瘤里面的细胞活得很“惨”,都处在珠穆朗玛峰那样的极度缺氧状态。
事实上,肿瘤恶性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生血管。一旦血管长出来,就使得这个肿瘤可以“滋润”地活下去了。而这件事情,无疑是与细胞对低氧的感知与响应有关的。
我本人的研究组曾经也做过一些涉及HIF-1的工作,而我的出发点也是癌症研究,具体说是癌症转移——这是恶性肿瘤的另一个生要标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死于癌症的病人当中,大部分都是死于转移产生的次发性癌症。也就是说,如果能阻断转移,就能拯救很多癌症患者的生命。而癌症转移的发起者,也正是HIF-1这双“手”,同样是低氧刺激所引发的。
今天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细胞低氧研究这个领域,无疑会对相关研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让我们未来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恶性肿瘤生血管以及转移的分子机制,为相关药物的研究带来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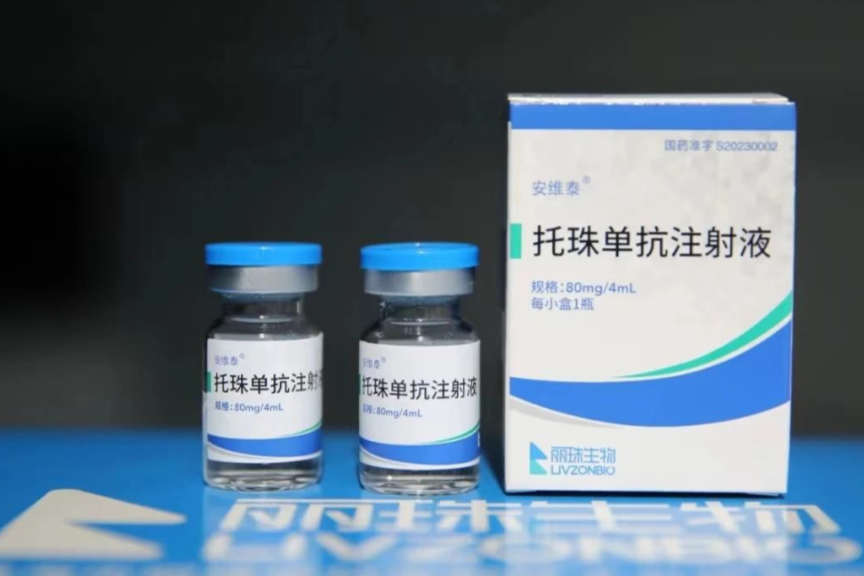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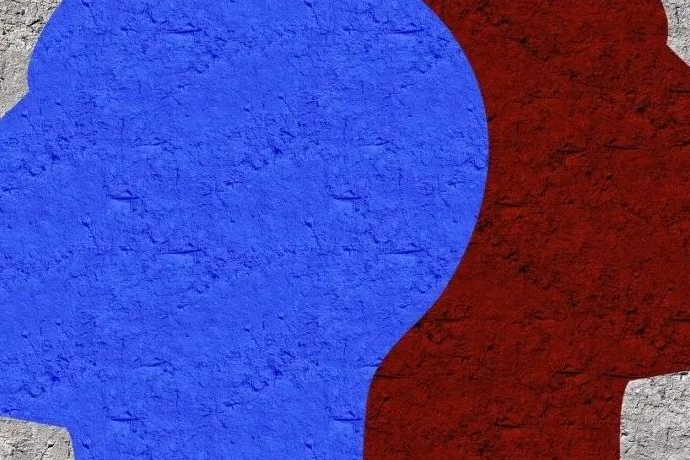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33011002015279
浙公网安备33011002015279 本网站未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产品信息
本网站未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产品信息
收藏
登录后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