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撰写《跨国药企成功启示录》和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深刻地意识到,创新药行业拼的是技术、投入和运气,所以被称为高投入、高风险的赌博;OTC(非处方药)和快消品行业拼的是企业对市场的敏感度、业务开拓能力和商业化能力,几乎是一种纯商业的行为,或者叫“生意”;而仿制药行业介于二者之间,拼的是战略战术、操盘能力和产品布局能力。目前,我国仿制药行业正处于“洗牌期”,战略战术、操盘能力和产品布局能力将决定企业的成败。而为了练就这些能力,企业必须先了解行业的发展规律、市场的运行逻辑、法律法规和国内外市场发展的状况与特点。
现代制药发展与人类寿命延长
有史以来,长生是人类从未改变的诉求,从秦始皇寻找仙药到道士炼丹,再到现代医学与生命科学探索,其终极目标都是实现人类长生。但基于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永生还只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理想”。尽管如此,高速发展的现代医药正在让人类一点点地“改命”。从提取汤剂到化学合成药物,再到生物制剂和基因治疗,人类在一次次现代医药的“革命”之中,寿命不断延长,生活质量也大幅改善。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数据,2021年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但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几岁,即便当今第一强国美国,在19世纪的人均寿命也仅有三十六七岁……
因为人类对“长生”的追求,所以有了医学和制药,虽然人类医药史已有千年,但以往千年的发展不及近100年的沉淀。所以故事就从100多年前的19世纪说起。现代制药业可溯源为提取天然药物和合成化学药物两大方向,提取药物历史较早,在19世纪初期就有公司开办工厂(如德国默克),加工并销售吗啡、奎宁和士的宁等生物碱,因为没有良好的制剂手段,剂型基本都是汤剂或酒剂,稳定性不好,服用也不方便,更不适于长途运输,制药公司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发展。另外,提取药物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受限于原材料,而且产品类型也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种容易提纯的药物。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首次制成了牛痘疫苗并在人体上试验,19世纪以后,提取生物制品(如灭活疫苗、血液制品、蛋白)也逐渐形成了产业雏形,自此,人类初步具备了对抗疟疾、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的能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益于化学和染料工业的高速发展,德国和瑞士的化工巨头开始用化学方法合成药品,乙酰苯胺、安替比林、阿司匹林、非那西丁、肾上腺素、普鲁卡因、巴比妥等划时代意义的分子相继被合成出来,人类疾病的治疗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现代制剂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突破,让药品的长期保存和长途运输成为了可能,到20世纪初,人类已经能够批量生产片剂、胶囊、丸剂和注射剂等现代化的剂型。随着药物的广泛普及和环境卫生条件的不断提升,美国的预期寿命在1900年上升到了47.3岁。
以往的新药都是在偶然中发现,而普鲁卡因的成功,意味着天然药物的结构可以被简化或改造,创新药的探索与发现路径又增加了一条,大大加速了行业的发展。随着化学药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从事提取汤剂生产的企业逐渐开始转型。20年代,因为流水生产线的引入,让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高,让现代制药踏上迅速而广泛普及之路,美国平均寿命史无前例地提高至54岁。
由于当时的卫生条件低下,感染是导致人类死亡的第一大要因,但此时的人类尚无有效的方法对抗细菌。1928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因发现了青霉素而燃起了人类对抗细菌的希望,但碍于当时的发酵技术的限制而无法量产。1932年,拜耳的化学家发现了磺胺的抗菌活性,并以“百浪多息”为商品名推向了市场。因为磺胺类的抗菌作用而被神化,最终导致了有名的“磺胺溶剂中毒”事件。二战爆发以后,因为没有对抗细菌感染的有效手段,大量的伤员在痛苦中死去,为了实现青霉素的量产,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带着青霉素的资料远赴美国请求帮助,最终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在1943年实现了量产。青霉素的量产是人类抗菌史上的伟大飞跃,同时也为创新药的探索与发现再次增添了一条全新的路径。由于青霉素没有专利,各国在二战后的几年里纷纷实现了量产,市场的蛋糕被迅速瓜分殆尽。为了守住既得利益,美国制药巨头们只能花重金开发青霉素的替代品,它们以青霉素的发现过程为鉴,派遣科学家到全球各地采集土壤样本,然后分离出细菌菌株培养研究,在短短几年间相继发现了氨基糖苷类(链霉素,1943)、氯霉素(1947)、四环素类(氯四环素,1948)、大环内酯类(红霉素,1952)、万古霉素(1952)和头孢菌素类(头孢菌素C,1953)抗生素。因为抗生素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细菌感染性疾病得以初步解决,美国的人均寿命在50年代进一步延长到68岁,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在1955年史无前例地达到了65岁。
抗生素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创新药黄金时期”,在抗生素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在四五十年代相继合成了糖皮质激素、苯二氮䓬类镇静催眠药、氢氯噻嗪、氯丙嗪、氮芥衍生物、组胺受体1(H1受体)阻断剂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据FDA统计数据,美国在1940-1960年间一共批准了413种新分子实体上市,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疾病治疗选择的同时,让制药业从化工业里被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门类。
60年代以后,创新药研发遇到了瓶颈,而且日益严格的药品监管环境让创新药研发变得更加困难,适逢当时多元化风靡全球,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开始疯狂多元化,创新药的发展热度由此走低,FDA统计数据显示,在1960-1980年间,美国一共仅批准了333个新分子实体上市,不仅数量上无法与此前1940-1960年媲美,而且创新质量上也存在明显的差距,除了β受体阻滞剂、免疫抑制剂、钙离子通道拮抗剂、肾上腺素转换酶抑制剂和组胺受体2阻断剂是首创外,大部分不过是迭代升级品或me too。
70年代以后,现代药物筛选技术、基因重组技术和单克隆技术的出现让药物发现的瓶颈被打破,与此同时,石油危机让化工业衰退,大部分化工巨头们将业务重心转向了制药,于是制药领域又兴起了一波研发热。因为效率高、投入低(约1-2亿美元),七八十年代被称为创新药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但随着审批尺度的不断提高,创新药的研发周期长达七八年,这些产品几乎在80年代以后才陆续获批上市。根据FDA的统计数据,在1980-2000年之间,美国一共批准了579个新分子实体上市,不但数量达到以往历史之最,而且有效地解决了人类三高(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首次被延长到75岁左右。
随着治疗水准的不断提升,90年代以后,创新药研发不再像黄金时代那么高产,研发成本因此而逐年飙升,巨头们为了保证盈利水平,只能不断提升药价。2000年以后,虽然FDA批准的新药数量有增无减(在2000-2020年间共批准了686个新分子实体),但是人类的预期寿命并未得到显著的延长。一方面是人类的最大死因癌症迟迟未攻克,20年的药物研发进展仅能够为患者带来几个月到几十个月的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是新世纪以来人们提倡“精准治疗”和“罕见病治疗”,每年虽有大量的药物获批上市,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患者使用。
高涨的医开支出与费用控制
如上所述,“长生”是人类的终极诉求,虽然人类目前尚无法实现“长生”,但预期寿命已经随现代医学的发展而得以大幅延长。《Protecting American’s health: FDA business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regulation》一书中提到:“19世纪初的美国人均寿命只有37岁,与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36岁)相当”,而现代医学产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部分发达国家已超过了80岁,日本更是超过了85岁。然而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带病生存期不断延长,随之而来是治疗需求的倍增。故现代医学让人类不断“改命”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医疗开支。另外,创新药研发成本的不断攀升,导致药价的不断上涨,进一步加重了各国的经济负担。近年来,因为经济增速的减缓,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医疗开支出现了失控的态势。
出生率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已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显而易见的规律,但出生率下降必然会导致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而且人均寿命越长,老龄化就越严重。由于人类适合劳动的年龄段是有限的,老龄化的结果是增加医疗负担,拖跨国民经济,使得医疗支出在GDP(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攀升。日本医药制造协会(JMPA)统计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里,发达国家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翻了2-3倍,美国在2020年的医疗支出竟高达GDP的19.7%。
当今发达国家几乎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的乏力的问题,而两大问题所导致的共同结果就是政府医疗开支和财政赤字快速增加。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富有预见性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控费”。由于药品支出是医疗支出的重要构成部分,控制药品支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各国“控费”的重要举措。而在控制药品开支方面,发达国家惯用的两种主要方式为品牌药价格谈判和促进仿制药普及与替代。因为高效的仿制药替代,2020年为美国节省的药品开支达3384亿美元,而美国同期的总处方药开支仅为348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仿制药替代,美国的药品开支可能在现有的水平上翻倍。虽然欧洲和日本的仿制药替代水平远不及美国,但由于近年来仿制药替代战略的有效实施,欧洲每年可节省医疗开支高达1000亿欧元(2016),而日本每年也可节省1.3万亿日元(2017)。
仿制药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仿制药与原研药相对应,泛指“模仿”上市产品而开发的产品,或上市产品的复制品。因为是“模仿”或“复制”,仿制药是依附品牌药的存在,只有品牌药专利到期后,它才会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仿制药的定义也不相同。美国仿制药没有法定的概念,FDA所采纳的 “generic drug”定义是剂型、规格、给药途径、质量、疗效特征和预期用途与参照药品(reference drug)一致的药品,“generic”一词源于拉丁语“genus”,意为通用的,既为“通用”,就不应被授予商品名加以区分。但事实上,美国一部分仿制药仍具有商品名,其中大部分是《Waxman- Hatch修正案》实施前批准的产品,还有一小部分是复杂制剂,如Mylan的Wixela Inhub(氟替卡松/沙美特罗吸入剂)、UCB的Parcopa(左旋多巴/卡比多巴口崩片)。在日本,仿制药被称为“後発医薬品”或“ジェネリック医薬品”,“後発医薬品”也只是相对“先発医薬品”而言的,也没有法定概念,PMDA所采纳的定义为“先発医薬品”(新药)专利到期以后开发上市的,主活性成分量与“先発医薬品”相同,且给药途径、安全有效性和用法用量也一致的药品。在英国和德国,仿制药甚至都没有确切的概念,仅是在注册上进行区分,主活性成分相同(API)、非活性成分(辅料)相似的产品就被视为仿制药。然而,仿制药在一部分国家也有法定的概念,法国的法定概念为与原研药成分和剂型相同、且生物等效的产品,意大利法律则限定为不受专利(含延长期)保护、且与原研有相同的活性成分、相同的剂型和适应症、生物等效的药品。事实上,这些概念都几乎是在八九十年代才提出的,并没有完全地兼顾历史。
尽管当今的监管机构普遍接受使用生物等效性数据来佐证仿制药与品牌药的疗效一致性,但仿制药在生物等效性理论成熟以前的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美国《Waxman- Hatch修正案》实施以前,仿制药也需要开展全面的安全有效性研究,1962年以前,FDA批准的仿制药仅是基于安全性的考虑,为此在1966年启动了“疗效再评价”。美国尚是如此,其它诸多国家在缺医少药或监管体系不成熟的背景下,低门槛地准入了大量的仿制药品,这些产品因为是模仿原研药开发出来的,但是它们并未经过严格的生物等效性检验,甚至都不存在标准的参比制剂,按照FDA的标准,它们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generic drug”。由于这些产品通常拥有商品名或商标名,所以也称为品牌仿制药或早期上市的仿制药,属于广义的仿制药范畴。
在笔者看来,狭义的“generic drug”是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控制过程中推行仿制药替代的产物,它的使命就是替代原研药,压缩药品开支。而品牌仿制药是仿制药发展史上早期阶段的产物,其历史意义是在原研未上市或不可及的情况下,充当市场教育的先锋,提高药品可及性和医生用药知识水平。美欧等发达国家因原研药可及性较高,仿制药的监管体系也成型较早,品牌仿制药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已很小,即便是现存的品牌仿制药也经过再评价,充分证明了其安全有效性。然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品牌仿制药依然广泛存在。IQVIA 2019年的报告显示,品牌仿制药占全球药品市场的20%,而狭义仿制药仅占9%。
综合上述,仿制药具有两大历史意义,一是提高药品可及性,二是仿制药替代。从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如药品可及性得到了解决,就可能向仿制药替代发展。在“提高药品可及性”的阶段,仿制药是稀缺或相对稀缺的资源,而进入“仿制药替代”以后,仿制药就可能很快成为过剩或相对过剩的资源,低价仿制药不但会替代原研,也会替代高价仿制药,这就是仿制药价格竞争的根本逻辑。
仿制药发展简史与仿制药替代
众所周知,欧洲莱茵河沿岸是化学工业的发源地,也是化学药品的发源地,在一战以前,德国、瑞士等国家就已经开发出大量的化学药品,而且几乎控制了全球80%的原料供应。一战爆发以后,欧洲的原料供应被中断,美国出现了药品短缺。为了摆脱对欧洲药品的依赖,美国化工巨头开始仿制或自主开发药品和化工品。一战以后,德国企业在海外的资产和专利相继被罚没,这为仿制药的开发上市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一战,德国的化工业受到巨大的破坏,美国趁机赶超了欧洲,成为化工和制药的领头羊,化学原料几乎不再依赖进口,而且当时美国的《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及修正案要求药品的成分写入标签,这使得仿制药拥有了标准的仿制对象。上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仿制药,公认为第一个仿制药品为阿司匹林。几乎同一时期,日本等工业实力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工厂,开始仿制西方药品。
1928年,美国医学杂志报道有少数药房使用相同成分的“仿制药”替代品牌药的现象,从此“仿制药替代”的理念初现雏形。在1938年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出台之后,要求所有药品在上市前都要提交NDA,“仿制药”也毫无区分地与新药一同审批监管。因为早期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存在疏漏,40-60年代,FDA批准的8605个“NDA”中,除了529个是新分子实体外,大部分都是“仿制药”或改剂型产品。而且这些仿制药品的审批,大多仅基于安全性数据,这是近4000个品种在1966年被要求再评价的原因。
40年代末,仿制药替代的概念正式被提出,但遭到了行业主流的反对,而且当时的技术和理论难以证明仿制药与原研药的一致性,加之当时行业的种种乱象,FDA对仿制药也心存芥蒂。最终,美国的各州陆续立法以反对仿制药替代,因为反替代法,美国仿制药一直处于压制的状态。然而在美国以外的其它地区,仿制药却得到初期的快速发展。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为了保障药品供应开始大力发展仿制药。
《Kefauver- Harris修正案》出现以后,新药和仿制药审批得到了极大的规范,美国出现了专业开发仿制药的公司。1965年,美国出台了公立医疗保险制度,政府开始关注医疗开支的问题,于是开始探索仿制药替代的可行性。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FDA于1966年开始对市售药品进行再评价,最终于1969年初步完成了3000多个药品的“有效”、“无效”、“需进一步研究”的筛分,为仿制药的扩大使用奠定了基础。70年代以后,FDA在增加仿制药审批的同时,还为寻找适合仿制药的审评路径开展了多种尝试,试图让仿制药提交简化新药申请(ANDA),并利用生物等效性指标来评估仿制药与对照药的一致性。在FDA探索仿制药审批路径的同时,各州相继取缔了反替代法,部分州还以替代法取而代之,让仿制药替代成为鼓励或强制性行为。除此以外,Medicare制定了费用控制计划,推出有利于仿制药的报销制度。1979年,FDA为了帮助各州有效地实施费用控制计划,建立了橙皮书,并于1980年出版发行。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数据,美国仿制药替代率从1980年的5.5%上升到1984年的9.5%,年节省药品开支从1.30亿美元增加至2.36亿美元。
1984年秋天,《Waxman- Hatch修正案》获得通过,FDA从此拥有了使用新路径批准仿制药的法律依据,而且持续了多年的“创新”与“仿制”的争议得以厘清,仿制药替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因为仿制药研发的简化,研发成本低至100-150万美元,于是很快就迎来了仿制药的申报潮,在1985-1989年间近有1800个ANDA获得批准,为仿制药的快速替代奠定了基础。在FDA开足马力审批的同时,美国CMS(Medicare和Medicaid服务中心)、FTC(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各州政府也都配套了有利于仿制药替代和扩大使用的措施,加之PBM(药品福利管理)服务机构在仿制药的流通链条中能更高比例的获益,在仿制药的扩大使用和替代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的“一系列举措”非常成功,仿制药处方量占比从1984年的19%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93%,2020年为美国节约的药品开支高达3384亿美元,节省率超过了50%。另外,在高效替代的同时,美国还利用增加竞争的方式让仿制药价格逐渐下滑,使得90%的处方量的仿制药仅消耗了18%的药品支出。因为成功的仿制药替代,在过去的19年间(2002-2020),美国节省的药品开支总额高达31930亿美元。
美国是仿制药替代最成功的国家,其成功的经验广泛被借鉴。于是在美国之后,诸多发达国家也兴起了仿制药的替代潮。与美国各州相似地,欧洲对仿制药替代的态度也有强制替代、鼓励替代、禁止替代和部分场景禁止替代等多种。1983年,英国率先提出了仿制药替代的计划,经过长达30年的持续推进,英国是欧洲仿制药使用率最高的国家。在英国之后,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陆续开展了仿制药替代的行动。但是欧洲因国家众多而体系复杂,英、德等国家仿制药渗透率已经超过80%,少数国家仍不允许仿制药替代。据欧洲仿制药协会(Medicines for Europe)的数据,2021年的仿制药平均处方量占比为67%,销售额占比为29%。
与美国所不同的是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以公立医疗保障体系为主导,政府是药品的直接或间接“买单人”,所以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控制药价。在药品定价机制上,国与国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在药品采购上,大部分国家都实施了集中招采制,但招采的频率、覆盖范围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导致了欧洲市场的丰富多样性,也是大部分仿制药巨头迟迟无法打开欧洲市场的一大原因。相比美国药价控制的“温水煮青蛙”策略,大部分欧洲国家则在国家的主导下一步到位,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符合国情的药价控制政策,例如法国要求仿制药定价必须低于原研药价格的60%以上,卢森堡更是高达70%。
相比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的仿制药替代政策都比较“刚猛”,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基本在10年内就完成。在政策的引导和强制之下,这些国家的仿制药替代率飞速提高,仿制药市场在2000-2015年间,先后出现了约10年的“井喷”式发展期,而在“井喷”期结束以后,市场仅有缓慢的增长、甚至多年无增长。虽然欧洲国家直接控制仿制药价格,但药价普遍较美国高,根据欧洲仿制药协会的说法,欧洲国家更加着眼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注重医疗支出、企业利润和政府预算之间的平衡。IQVIA数据显示,近5年来,欧洲Top 5市场的仿制药平均单价有略微的、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当然这其中也有产品升级和迭代的因素。另外有文献报道,英国和德国等国家仿制药销售价格较高,但出厂价较低,因为普遍存在“折扣”的行为。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第一个推进仿制药替代的亚洲国家。因为日本的药品较为混乱,在上世纪已经开展了多次再评价。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几乎停止了增长,严重的老龄化让医疗开支逐渐趋于失控,于是在1993年提出了扩大仿制药使用和替代的战略构想。1997年,日本启动了一致性评价,开始统一标准,2002年,扩大仿制药使用的战略正式提出。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日本跟法国一样是品牌药忠诚度极高的国家,为了推进仿制药替代,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量的鼓励措施,为仿制药流通链条提供各种利益补偿。2013年之后,在引导的同时逐渐加入强制措施,以确保完成“仿制药替代率在2020年达到80%”的预定目标。在仿制药战略出台之初,政策对仿制药行业普遍利好,市场得以飞速发展,但随着替代率的逐渐提升和市场机制的基本形成,日本开始频繁调控药价,仿制药企业逐渐感到无力可图,2016年以来,日本仿制药市场出现了跨国巨头逃离,本土企业出海的现状。
综合上述,美国的仿制药政策是通过自由竞争实现药价下降,因为市场较大,仿制药替代最为彻底,给仿制药市场带来了近30年的发展期。德、法、意。西、日等国家因为市场较小,无法充分发挥竞争效应,而且这些国家都以公立医疗保障体系占主导,所以政府主导着药品价格。在政府政策的控制下,这些国家10年左右就基本完成了预期的仿制药替代,价格也实现了大幅下降,但替代并不彻底,仍有大量专利失效的品牌药在市场上销售。
在日本之后,我国也推行了仿制药的替代。2009年,我国实施了全民医保制度,但随着该制度的实施,我国医疗支出快速增长,医保结存率逐年下降,2020年的医疗支出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12%,几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我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不得不将医疗费用控制提上日程。为了推行仿制药替代,我国在2016年开展了一致性评价,而为了实现医疗费用控制和支付结构转移,2018年又推出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集采)制度。虽然我国的仿制药替代实施较晚,但在符合国情的条件下,欧美日的成功经验都可以被借鉴使用,使得药品价格迅速下降同时,仿制药替代率也随着集采的推进而快速升高。
然而,与欧美日所不同的是,我国一直是一个以仿制药占主导的国家,IMS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的仿制药销售占比为58%,是世界第二大仿制药市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仿制药质量标准较低,质量参差不齐,专利失效的品牌药仍占据着20%的市场。由于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我国不需要“通过替代实现控费”,而是“在控费的过程中实现替代”,而控费的主要目的砍掉药品在流通渠道中的价格加成。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6批国家集采,涉及近240个品种,自2018年实施以来,已累计节省费用超过了2600亿元,如按约定采购量测算,则每年节约药品费用1016 亿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在2025年前要完成500个品种的集采,而前500个品种几乎占据我国仿制药市场的90%,故我国仿制药价格控制和仿制药替代有望在未来3-5年内初步完成。
丰富多样的全球仿制药市场环境
对于创新药企业而言,在成本升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来保障盈利水平,但对于仿制药企业而言,成本升高意味着丧失竞争力。因为仿制药不是稀缺的资源,所以仿制药企业并没有议价权,而且仿制药的价格会随着仿制药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准入门槛越低、市场规模越大的品种,价格竞争就会越激烈。为了保证盈利水平,仿制药巨头通常会瞄准率先上市的机会、开发差异化、高准入门槛、小众化的产品、有选择地进入优势市场来避开竞争的锋芒。与此同时,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他们通常也会控制原料来源、优化供应链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一系列成功的运作,Teva和Sandoz等仿制药巨头的盈利能力相比上世纪90年代都稳中有升,但也有诸多仿制药企业因一着不慎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根据IQVIA 2019年的报告,仿制药占全球药品市场的29%,其中非品牌仿制药为9%,而品牌仿制药占20%。按照当前的全球药品市场估算,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在4000亿美元上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但这4000亿美元的市场广泛分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又极具多样化,客观地了解市场、并有选择地进入自己擅长的市场,根据市场的情况建立接地气的特色产品包,是仿制药业务成功扩张的关键所在。
如上文所述,仿制药起源于美国,同时美国也是最早推进仿制药替代国家。因为高效的仿制药替代,美国仿制药的价格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一般的仿制药价格已经低至无利可图。由于美国一味追求仿制药的价格竞争,仿制药市场在2015年以后呈现出逐年萎缩的态势,如今市场规模约680亿美元(出厂价),相比2015年的巅峰已经萎缩了近20%。为了对抗价格冲击,仿制药巨头通过建立领先的技术平台来开发高技术门槛的产品,但随着仿制药企业的不断技术升级,这些所谓的壁垒逐渐被广大企业攻破,它们再也无法守住既得的市场份额,美国仿制药市场的竞争格局由十年前的“低集中度向高集中度转变”过渡为“高集中度向低集中度转变”。
随着美国市场的不断萎缩,欧洲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市场。虽欧洲拥有近700亿美元(出厂价)的仿制药市场,但是零碎的分散在约50个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语言文化、政治倾向和药品政策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为跨国仿制药企业的产品准入和市场运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虽然德、法、意、英、西等top 5国家集中了欧洲50%-60%的市场,但这些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很少有跨国仿制药巨头同时能在三个及以上国家建立起遥遥领先的优势。但欧洲这种琐碎的市场也有效地分散了竞争,仿制药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和长远的发展战略,有选择地进入部分国家。整体而言,欧洲的仿制药价格仍高于美国,而且替代率也没有发展到极致,另外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注重医疗支出、企业利润和政府预算之间的平衡,在未来五到十年里,欧洲市场仍会保持低速增长。
亚洲方面,日本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市场,由于日本大力推广仿制药普及和替代,仿制药市场规模在短短的20年里翻了8-9倍,在2020年达到了175亿美元(报销价),但由于日本政府近年来频繁地控制药价,让仿制药变得无利可图。一方面,日本价格谈判和降价机制,让品牌药价格几乎已经是发达国家中的最低,而仿制药的定价则以品牌药的40%-50%作为天花板,而且每年都有降价要求;另一方面,日本没有统一的采购机制,仿制药也需要学术推广,并不像欧美那样生产出来就能卖掉。因为日本市场的诸多特色原因,国际仿制药巨头一直未打开日本市场,而且还有外逃的趋势。对于日本本土仿制药企业而言,跨国巨头外逃或许是个好消息,但频繁的药价控制也让他们的利润持续下滑,逼着他们出海开拓新市场。
对于发达或相对发达的药品市场而言,发展仿制药是为了替代与控费,而对经济欠发达国家而言,仿制药的主要意义是提高药品的可及性。由于发达国家原研药可及性高,几乎不存在药品可及性的问题,但是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大部分国家存在或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在“缺医少药”的国家或“缺医少药”的特定历史时期,政府通常会制定有利于仿制药发展的政策,以迅速提高药品可及性。纵观当今世界,仍有30-40亿人口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部分国家还没有自主的监管体系,甚至还处于小作坊生产药品的时代。
综合上述,根据仿制药品市场的成熟程度,可分为发达市场、规范市场、非规范市场和非法规市场四类。1)发达市场(如美、德、英、日)监管体系完善、市场机制成熟,基本实现了仿制药替代;2)规范市场(如中、韩、印、巴)监管体系完善、市场机制相对成熟,已具开展备仿制药替代的条件或正在推行仿制药替代;3)非规范市场(如拉美和亚洲大部分国家)监管体系相对完善、但市场机制不成熟,还存在着一定缺医少药的问题,不具备仿制药替代的条件;4)非法规市场(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无独立的监管体系,存在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通常需要借助发达国家或世卫组织的认证体系来控制药品质量,部分国家甚至还处于小作坊生产药品的时代。
在发达市场,仿制药行业资源过剩,竞争非常激烈,平均药价一直处于下行区间,美国因仿制药处方量占比达到极限而市场逐步萎缩,英、德、加、西、意、日、澳等国家因政策的原因而竞争压力稍微缓和,而且仿制药替代率也未达瓶颈,在短期内(如5年),还具有缓慢增长的空间。在规范市场,市场规模在中长期内(5-10年)会因各国大力发展仿制药替代而逐步扩大,但药价也会因替代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快速下降。韩国、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将是未来10年里,仿制药销量的增长极,其中我国和巴西可能会因为费用控制而出现市场波动,但可能会很快“触底反弹”,然后进入持续增长的区间。此外,在非规范市场和非法规市场生活着30-40亿人口,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着药品可及性的问题。截止目前,FDA已批准了2000个新分子实体,扣除已退市的品种和加上新复方制剂,大部分发达国家在销品种数量在1800-2500之间,如果一个国家在销品种数量低于1500个,就可能存在药品可及性不足的问题,然而世界很大一部分中低收入国家的市售品种数甚至不到800个。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他们需要从“解决药品可及性”到实现“仿制药替代”,将是未来仿制药市场的远景所在。
仿制药后的另一场盛宴:biosimilar
如果从广义的仿制药定义而言,biosimilar也应属于仿制药的范畴,故也被称为生物仿制药,但biosimilar与化学仿制药不能直接等同。首先,生物大分子较为复杂,不但具有一级结构,还具有二级和三级结构,单纯的氨基酸序列结构(化学结构)一致,并不能等同于安全有效,更别说疗效一致;其次,通过临床试验验证后的biosimilar虽然安全有效,但不像化学仿制药一样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另外,biosimilar基本都有商品名,性质上不同于generic drug。根据美国的《生物制品价格竞争和创新法》(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 BPCIA)要求,生物仿制药必须高度相似,与参考药物没有显著性的临床差异,必须进行免疫原性、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研究,还有可能要开展药效动力学研究,biosimilar也按BLA(biological license application)路径申报,而且只能在参照药物获批4年后提交申请,上市12年后批准。
Biosimilar始于本世纪初,源于基因工程技术和单克隆技术成熟后的第一波上市产品的专利悬崖。2006年,欧洲医药管理局(EMA)批准了两个生长激素的biosimilar而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FDA因为没有找到评估“仿制药品”与“对照药品”之间一致性的有效方法而迟迟不敢开绿灯(简化批准程序),直到2015年,美国才批准了首个biosimilar上市,而在2006-2014年之间,EMA已经批准了21个biosimilar,产品涉及促红细胞生成素、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非格司亭)、英夫利昔单抗、生长激素、卵泡素和胰岛素(美国视为化药,其仿制药归为505b2)等产品,甚至有部分医疗费用控制的国家(如德国)已经将biosimilar纳入到替代计划。
自人类进入生物技术时代以来,FDA一共批准了180余个新生物药(不包括血液制品、疫苗、蛋白和细胞制品),但这些“为数不多”的生物制品却占据了全球三分一的药品销售额,市场非常巨大。而这180多个品种中,1980-2005年之间批准的产品有65个,这些产品几乎都已专利失效或即将面临专利悬崖,若除去被市场淘汰的和因不良反应退市的产品,有价值开发为biosimilar的产品约30个,2030年市场规模可达1300亿美元。
巨大的商机早已让仿制药公司垂涎,但碍于技术壁垒、研发投入和审批路径的原因,很多企业早已望而却步。早在2010年以前,Sandoz、Watson和Teva等仿制药巨头已经开始布局biosimilar,但生物技术并非是化学仿制药企业的强项,而且biosimilar高达上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也足以让一般仿制药企业望而却步。最终大部分仿制药公司的biosimilar项目不是中途流产就是长期搁置,只有Teva、Mylan和Sandoz等为数不多的仿制药巨头坚持了下来,而且三大仿制药巨头中,只有Sandoz目前处于领先优势。根据诺华的年报显示,Sandoz的biosimilar销售额已超过20亿美元,占到仿制药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相比之下,Teva与Mylan的biosimilar还未形成规模,在仿制药销售额中的占比仅有5%左右。
除了仿制药巨头,辉瑞、安进、渤健等创新药巨头利用生物技术的领先优势也强势切入到biosimilar市场,而且很快成为了竞争赛道的领跑者。尽管Teva、Mylan等仿制药巨头在奋力追赶,但biosimilar也会像化学仿制药一样随着获批数量的增加而价格逐渐下降,待他们追上时,辉瑞、安进、Sandoz和渤健可能已经吃尽的碗中的肉,剩下的只有稀汤。
Biosimilar市场前景好,蛋糕足够大,增长也足够快,必然是化学仿制药盛宴结束后的另一场盛宴,也是化学仿制药企业转型的一大选项。但biosimilar可“仿”的产品较少,目前有价值开发的biosimilar的品种一共就二三十个,赛道必然异常拥挤,然而生物制剂的市场通常以高价为支撑,销量一般都很小,如果有10家以上的企业同时推出biosimilar,各家分到的平均销量可能只有几千到几万支,甚至部分品种可能只有几百支,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之下,必然无利可图。因此,biosimilar的布局必须差异化地选品,以保证拟立项品种的赛道领先优势,并有选择地进入某个市场。
全球新形势下仿制药企业的生存之路
综合上文所述,仿制药的是“模仿”品牌药而开发的产品,并没有专利或法规赋予其长期的市场独占性,注定不是市场稀缺的资源。由于准入门槛较低,仿制药很容易被竞争产品替代,制药企业为了守住市场份额,降价在所难免。事实已经证明,仿制药的价格因仿制药批文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而仿制药批文的数量则取决于产品的准入门槛的高低和拟仿制品种市场规模的大小,因此处方量越大、准入门槛越低的品种,市场竞争就会越激烈,价格也自然会越低。所以在美国,“大品种”和“小品种”的仿制药销售额几乎都是几百万到几千万美元。
由于发达国家广泛通过“推行仿制药替代”、“促进仿制药竞争”来控制药品支出的增长,美国、欧洲、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巴西和加拿大等成熟或相对成熟的市场,仿制药价格都呈现出普遍下降的趋势。而价格下滑所致的结果就是市场萎缩或总利润盘缩小,仿制药企业只有不断布局新品(尤其是高门槛、差异化的产品)才能维持业务的增长,在竞争过于激烈、开发新品也无法维持业务时,企业只能开拓新市场或转型。在美、欧、日、中、印、巴、加之外,全球还有40亿人口和1500亿美元的仿制药市场,如何在这200多个不同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监管体系的“琐碎”市场中筛选出蓝海区域并建立特色产品管线,是近年来仿制药巨头保障盈利能力的一大关键。
虽然近年来兴起的biosimilar被视为化学仿制药之后的下一场盛宴,但biosimilar并不适合普通仿制药企业布局。一是biosimilar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大,一般仿制药企业不具备开发条件;二是biosimilar的仿制对象较少,销量小,未来的价格竞争依然十分激烈,能够真正盈利的可能只有处于赛道领头地位的企业;三是biosimilar研发周期长,仿制药企业现在才开始布局,几乎很难占据赛道的优势。因此,biosimilar的机会只属于少数企业和少数人。对于一般仿制药企业而言,开发高壁垒的产品、建立差异化的产品管线、优化供应链、产线升级、选择蓝海市场出海或许是更可行的措施。
目前,我国仿制药行业正处于洗牌期,资源已经明显过剩,仿制药企业必须要熟悉行业的发展规律、运行逻辑和国内外市场的状况,积极地转型、整合、出海。为此,笔者总结了十余家企业的发家历程,生存状态,基于时势变化和企业自身情况的风险评估、战略规划和产品线打造的经验,为广大读者带来参考或借鉴。最后,笔者希望《圣经》里的一句话能让各位读者有所启示——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本文内容为笔者新书《仿制药帝国的崛起与没落》第1章的节选,未经作者本人亲笔授权,本文不允许任何媒体转载,否则一律视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由于内容尚未正式出版,关键性数据和参考文献已经被隐藏,以上内容为初稿,可能有错别字或表达不当的地方,欢迎广大读者指出或参与讨论,笔者微信:voyager88。
魏利军,前哈药集团产品战略总监和产品立项部总监,在过去三年中成功立项30个,并成功组建了哈药北京创新制剂研究中心。在各种杂志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代表著作为《跨国企业成功启示录》。新书《仿制药帝国的崛起与没落》(书名可能会调整)已经在出版社编辑阶段,预计春节前后正式出版发行,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与帮助。该书主线为仿制药企业的战略规划,业务转型和产品布局。全书22章,版面字数约50-60万字。第一部分(前五章)讲述仿制药法规的衍化逻辑和市场形成机制,以及全球主要仿制市场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第6-20章)讲述了15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发家模式的仿制药企业的兴衰成败,重点介绍了他们随环境而变的风险评估,战略规划和产品线布局的逻辑,第三部分(最后两章)分别讲述我国仿制药政策的演化、市场市场形势与特点,我国仿制药企业结合国际情况的转型思考,特色化产品线规划和产品选项思路等。
相关阅读:
《仿制药帝国的崛起与没落》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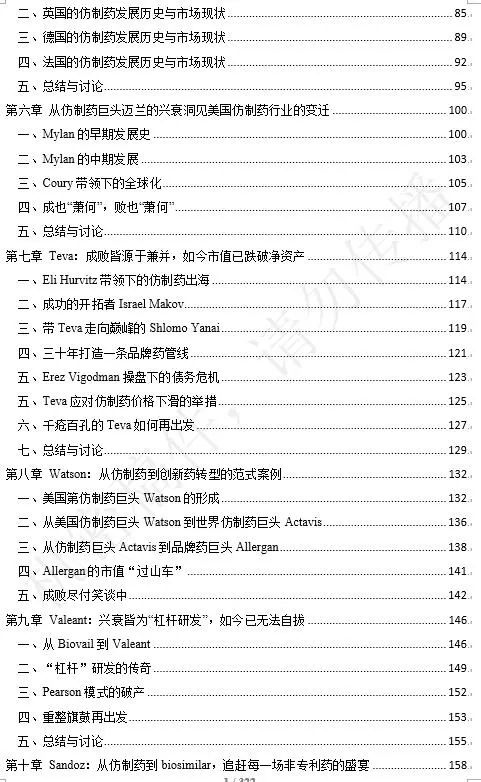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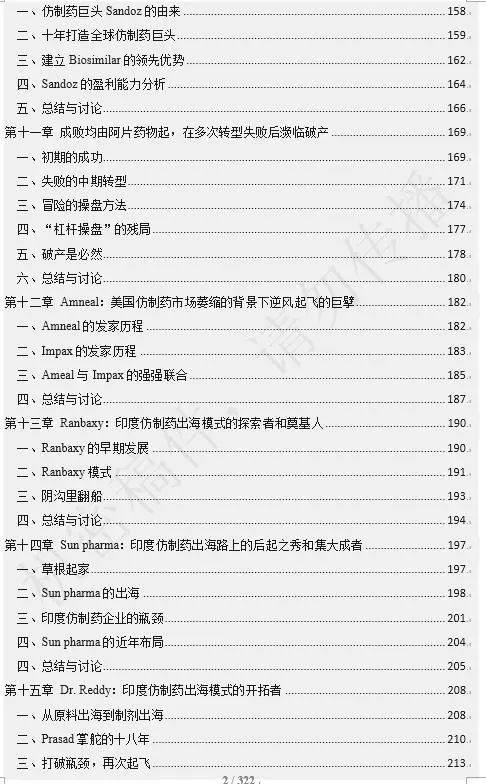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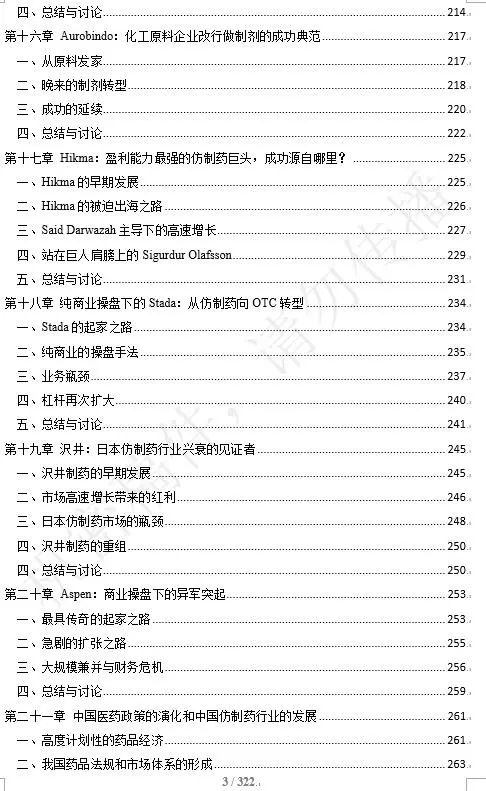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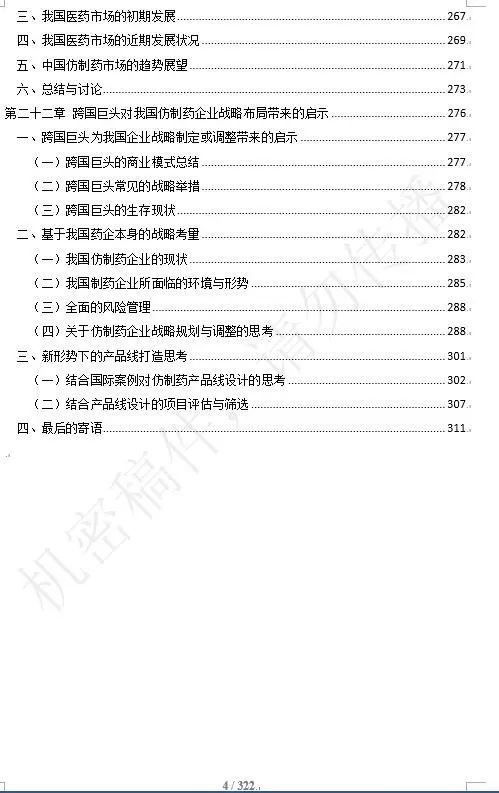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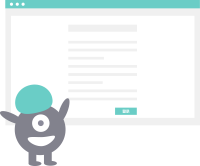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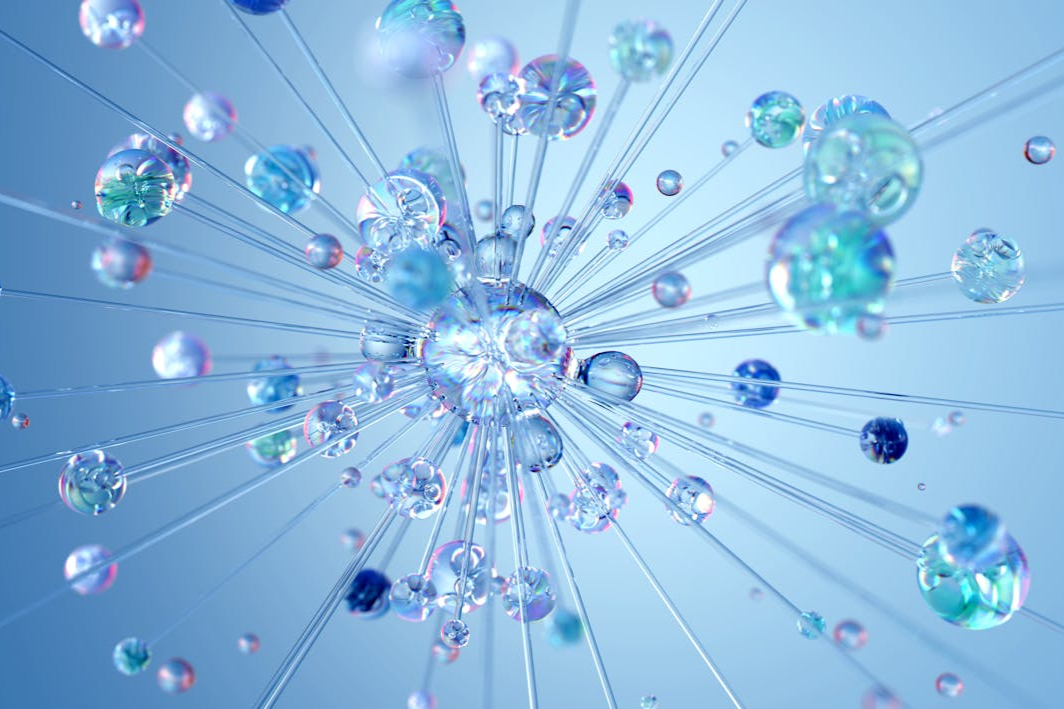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33011002015279
浙公网安备33011002015279 本网站未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产品信息
本网站未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产品信息
收藏
登录后参与评论
暂无评论